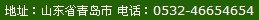|
北京中医皮肤科医院 http://pf.39.net/bdfyy/qsnbdf/160304/4780753.html 四川省散文学会主办 《四川散文》联合办刊和指定选稿平台 爹是谜来我是雾 ●刘思树(四川) 那首歌儿唱的“你是风儿我是沙”,忽然想到用“爹是谜来我是雾”来描述我与我爹之间的情缘再妙不过了。 百度中对“爹”的详解中是这样表述的:爹,即父亲或爸爸之意。一般在我国过去的时间段内称呼父亲为爹的较多,或者城市工农阶层称父亲为爹的也较多,或者农村称父亲为爹较多。又解,父亲:爹妈、爹娘,可以给人更亲切的感觉。 “爹”,是我川北老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对父亲的最最尊敬的尊称了。称“爸”的,好象是隔着好几房的人了一样。因为,除称父亲为“爹”外,还称父亲的亲弟兄为“×老子”。如父亲是三弟兄中老大,那我就直称他两弟为二老子、三老子;如父亲是三弟兄中老二,那我就得称他哥为“大老子”、弟为“三老子”或为“幺老子”。称“爸”的就要轮到隔房人去了。即同爷不同父、同祖不同爷等那些本地与父亲同姓同辈份的人,而且还必须在“爸”字前面加上姓名,如“××爸”或“×××爸”。 自从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城里知识青年下乡的影响,他们不但把城里比较洋气“爸”带下了乡,还把城里的普通话也带到了乡村田野。一些赶时髦的当地青年逐渐把“爹”转任成“爸”,还在田间地头山旯旮里飘着广播里那种北京普通话。只是当时的“爹”们不习惯,咋听都不象亲生的。现在对父亲的称谓都很随意了,除普遍称爸外,还有称老爸、老汉、老太爷、老爷子的等。虽然我也当了几十年爸了,但总觉得还是没有“爹”要亲切些。 爹是谜来我是雾,主要是指我爹的成长给我是一头雾水的感觉。我以为我是最了解我爹的,因为我是睡在他脚头长大的;我小时放牛腿摔折了,是医院;夜间我同他一起敲梆梆,看过玉米地,看过棉花;我同他一起起早贪黑耕田耙地挣过工分;我还晓得他晚上用自制的竹筒小解,我还帮他倒过好几回;我跟他一起熬更守夜去给人家做过灵房;我跟他一起上山看田守水抓过鱼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历历在目。 从我记事起,我就晓得爹爱留个小胡胡、爱穿长布衫的老人了(那时还有留“清朝辫子”的老人呢,但我爹没有),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爹就已经四十八岁了。那时凡是听说某某某四十多岁了,在我幼小的心目中都是老人辈了。每次赶场、开会、吃酒出门前,母亲总是亲手将新做的或洗得干干净净、且叠得整整齐齐的长布衫拿给我爹,还亲手帮忙给我爹穿上,还用桑杆子(高梁杆尖尖做的)在爹的前胸后背扫个抻抻展展,才让其出门。不知道我爹当时是什么感受,现在我爱人有时也这么给我做(当然不是桑杆子了),我还不耐烦地闲她啰嗦。她说,你妈不也这么做的吗?! 爹在我心中一直都很敬畏。上学读书前都不(敢)知道爹的姓名,也不知道爹就是家长,以至于报名老师问我家长叫什么名字我却说不知道。自己不敢去碰爹名字中任何一个字,哪个同学敢拿爹的名字开玩笑,立马给他“毛起”(比发火还严重的行为)。爹在我心中一直都很威严。他虽然没有打过我,但他要我做到的事不敢说不也不敢拖,就从这一点上他在我心中多少还留有那么一点怨恨。母亲虽然狠狠地打过我几回,但她说的事我不乐意时是能拖则拖,以至于拖到最后她自己都忘记了,所以母亲在我心中是最好的人。爹在我心中一直都很正直。生怕耽误集体的事和人家的事,以至于母亲主持我家第二次建修住房,工人都上房了父亲还是不同意,怕影响集体修水利的劳动力。在那次“斗私批修”会上,爹把剥了集体棕树上几片棕叶回家作牛绳都抖了出来,还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而人家偷树卖的人没说出来也就过去了。爹在我心中一直都很简单。家里哪块田地种啥栽啥都要问母亲咋安排的,以至于那一次他已把牛扎在地里了又把牛唤下,跑几里路去问了母亲才重新回来做地。 我觉得爹是一个谜,还是前几年我回老家收集族谱资料才感觉到的。从老人们零零星星的传说片断中,我窥视出我家祖业上的不凡和我爹不一般的成长谜团。我爹手上有门手艺活就是扎灵房子,也就是给去世的人修到阴间去住的房子。据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传说,扎灵房这个很重要,如果不这样做,去世的人到了阴间没房住,就要给阳间的人托梦,还会让阳间的人三灾八难过得不安宁。在我看来这是迷信,但在爹们那一代人做得很认真。在那个年代“扎灵房”是定为“封资修”的范畴,我爹被人请去帮主人家完成心愿,都是在夜深人静偷偷摸摸躲在楼角里且从不收钱。自从我有本事折纸飞机了,爹做那活时就把小小的我带上去帮他糊纸。冬天老人们“走”得多,做纸活又不能生火,那个手冷脚僵啊!那年要不是祖国南疆战火起,我也不会披挂带枪上战场,我把我爹这事业继承下来,在今天我就可以做成一个产业,能赚多少钱不好说,反正有一个县级宾仪馆馆长,仅这个产业项目给他送礼就是30万元。好在我今天做的活与我爹那活都属于文化产业类,这也可能就是基因在传递过程中的转换吧。今天我也和我爹一样,他那时做活不收钱,我今天写点文章也不收人家的钱。不过我爹不收钱,后来在我家修房用工上得到了蜂拥而至的回报;我这写点东西不收钱的活,好久才能有回报呢?!哈哈哈…… 说起我爹能得到这门手艺,也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获得的。我爹是爷爷的独儿子,爷爷又是祖祖的独儿子,再往上两代祖先都是向外家抱养的独儿子,再再再往上那代祖宗在当地可算是大地主了。小时候,父亲随便手一指就说那遍田、那遍地、那遍山,原来是我们家的。发财不发人这个规律似乎在那个朝代挺灵的。到了我爹养我们大小五个小家伙和供养两老人的时代,我们家的财富操持得就只剩下个“贫下中农”水平了。所以,我在编写我们族谱时,我怎么也想不通我爷爷怎么会让我爹过上那样凄惨的童年——他可是两代无后、二代单传的独儿子啊!据说我爹被爷爷赶出家门时才七八岁,我爹不知道怎么的就流浪到距家00多公里(广元旺苍)的山河里。这段历史从没听我爹讲过。说我爹到了山河里被一家好心人收养并为其放牛,不知怎么的,后来我爹又到了距我们家二十余里的一个叫黄金口的场镇上一户人家,这家人正好会做灵房子活,我爹就把这门手艺学到了手。据说我爹是爷爷婆婆老了想儿子了才去找着认了回来的。 按理说,我爹有这样的经历对家庭应该有叛逆的表现,然而从他后来的行事看,他的乖巧让人无法想象。婆婆爷爷旧俗意识严重(这也许是他仗着是三代人指望的一个独生子养尊处优惯出来的吧),父母们走路脚步迈重了、走快了都要受到他们的训斥;集体做工走得再早、回来得再晚,父母都要跪在他们床前行礼告别、请安,都要陪他们坐坐说说家里外头的话。在婆婆快要落气(去世)的前一天,爹妈再三央求她老人家还想吃点啥,婆婆说就想喝口酒,你们是办不到的。从不开口给干部找麻烦的爹妈,拿着家中藏着的仅有的两把面条,硬是去求情弄了二两酒票,把酒给老人喝到了嘴里。爹妈老的时候那几年,我也尽可能地利用节假日克服外出旅行游览的欲望,陪伴在他们身边,讲讲他们给我们小时候讲的那些故事和笑话,也充分理解母亲“老了,吃啥喝啥穿啥都不想了,总想养的你们几个就像抱的一窝小鸡一样,能天天跟在身边转……”这句话的含义。 在我爹八十岁那年,部队批准我转业提前回家联系工作。年前几次在县城、市里联系工作无果后的年后,又一次出门讨工作之时,父亲拄着拐杖把我送出老远并嘱咐我早点回来。由于前几次的失利我已带着不耐烦的情绪,说我该要把事情落实得差不多了才行嘛!由于我出去后居无定所,等我经过广元、元坝返回到剑阁县城舅舅家已是第四天的时间了。舅舅告诉我,爹就在我走后的第二天晚上患脑溢血已经去世了,等我赶回老家,大前天还送我、让我早点回家的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那冰冷的棺材里了。 回想我爹离开我已经二十多年了,要是他在天有灵看到我的这一切,绝对觉得我是一个怪物。有句俗话说:“老大傻,老二奸,家家有个坏老三”,而我就是那个弟兄中的“坏老三”。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他们拆除旧时茅房修瓦房,他们忙时我也忙,他们忙着请人用工挑土筑墙,我忙着在临时搭建的草棚子里爬出爬进。不知多少次他们不得不丢下手中要紧的活,一次又一次地将尿泥满身、眼珠溜溜转的我塞进稍显安全的草棚子里,不知他们有过多少回决心要将我这个已是姊妹第五个的“坏老三”交给哪个算了。我爹也没算过他睡过我多少尿过的床、也看见我“儿童团”时出演过的“鸠山”、也欣赏过我给牛充“老子”时鼓起的眼珠比牛眼还大的形态、也被我捡回的那个“舅舅家的冬瓜面”的龙门阵笑得泪水长流……他老人家虽然没有享到我的福,但当我穿上军装走上战场时、当从前线误传回我头进了子弹腿打折了时、当我立功受奖传回捷报时、当我退婚离婚又重建家庭时,也没少给他带去惊悚与慌张乃至稀罕,到今天我爹如在那边看到我这个“怪物”的“坏老三”,嘴角绝对会露出复杂的不可言状的微笑。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刘思树(微名:爱了武装爱红装),四川广元剑阁人,市县作协会员。入伍十余载,现就职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交通运输局。历经部队电影放映员、战地宣传员、四川汶川“5.1”特大地震交通抢险报道员。曾获三等战功,时有图文作品登载于报刊网络。 《天府散文》编委成员 总编:胡大奎 主编:唐明霞 审稿:周联合 编委:张小明李红军姚佳梁有劳 投稿邮箱: qq.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ezx.com/jgxzx/10249.html |
当前位置: 剑阁县 >天府散文刘思树爹是谜来我是雾
时间:2022/2/2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关于拟命名剑阁县第七批家庭农场县级示范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