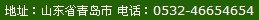|
全国白癜风公益救助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027/5796518.html 县志上记载,通真观在“县城东南十五里、在新城旧卧虎闸南半里”。还有几条信息可以参照: 放水桥,在通真观北。歙人汪喜起重修。 留云亭,在通真观。 明兵部尚书单安仁墓,申《志》云:“在旧江口,通真观东隅。” 解读是:通真观在放水桥的南面,通真观里面有个“留云亭”,通真观在旧江口,其东侧有单安仁的墓。 年7月15日,为撰写《诗话十二圩》积累资料,笔者与历史文化爱好者金小平、张向阳、郭玉波一道,顶着烈日,沿着古珠金沙河,对新城与旧港之间的观音庵、月宫庵、梅花院、通真观等处遗迹进行了实地探访。 在沙河拐弯处,我们走访了94岁的陈凤英老太太,她属鼠,推测应为年出生,金桥人,20岁左右嫁到此地。陈老太说,此地就是通真观(属于十二圩越江村常庄组),嫁过来的时候通真观还在,有前后大殿,内有牛头马面,有一位看护观产的道士,是个“湖南蛮子”,通真观南面偏西一点有一口约一亩地水塘,塘前有一座亭子,亭子已经破败,里面没有东西。东边有没有名人的墓?记不清了,好像没有。通真观曾做过越江大队的大队部,旧有建筑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拆毁的。 老太不仅确认了通真观的地址,而且还证实了县志上记载的“留云亭”的存在。 老太的邻居也向我们展示了从原来的废墟上找到的瓦当,据称是通真观遗物。 笔者曾于年3月21日,在仪征收藏家厉俊(仪征厉氏后裔)的“崇古斋”,见到过光绪十七年()仪征名人张丙炎(-,字午桥,号药农,一号榕园,咸丰九年进士,官至肇庆知府。父亲张安保为《道光重修仪征县志》总纂)为悟阳子重建通真观而题写的石额,这个石额说明,至少在光绪十七年(),通真观里的道长“悟阳子”还在发起重建并且成功建成,修葺一新的通真观还延请仪征著名人士张丙炎题写了观额。 县志记载,通真观又叫通真万寿宫,位于县城东南十五里、新城旧卧虎闸南半里,是在元朝大德年间,由五老峰人雷希复始建的。后来逐步荒颓。明朝洪武年间,致仕在仪真养老的兵部尚书单安仁,令通会路通玄重建。永乐年间又被毁,后又重建。弘治年间,再建,由于通真观地处滨江,经常经受水患,屡修屡圮。天启三年(),邑人汪钺重修。 元朝翰林程巨夫(山阴人,官行台侍御史,著有《程雪楼文集》),为真州通真观写了一篇《记》,记中说到:道家讲究无为,但又说无不为,这就如同水流一般,无为就像静止的水面,无不为就像流动的江河。众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或佐君平天下,或修身养性,各得其所。当世做的好事,后世必得赞扬。我是郢地人,曾听父老们说起,有一位真牧先生,潜心道教,离开家乡顺江东下,在九宫兴建了瑞庆宫,他的徒弟孚惠先生,在浔阳兴建了寿圣观,至今香火很盛。我听了以后,牢记在心。后来我出来为朝廷工作,来到了江淮地区,看到了洞渊法师雷君在白沙(仪征别称)兴建的通真观,他还说,这是在从前我师父孚惠的祠堂基础上建起来的。孚惠当初为大家驱邪治病有功,百姓怀念他的功德,给他建了祠堂,然而仅百年左右,祠堂就没有了。仪真这里原本就是江海汇聚之地,地基都是泥沙,雷君不怕困难,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夯土、基石、木桩、夹板,从打牢基础开始施工,从至元甲申(二十一年,),到大德丁酉(元年,),前后用了十四年,建成了殿堂、门庑、房室、庖库、园田、仓庾等建筑和设施,道观必备的功能都已具备,建成后的通真观,与九宫瑞庆宫、浔阳寿圣观齐名,可谓盛矣!我不禁感叹:道理和学问无论大小,关键在于传承啊。能够几代人持久不断地诠释道义,才能将事业延续和发展下去。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和发自内心的感受。看今日之雷君,身为崇尚“无为”的道家子弟,而实际在践行“无不为”的理念,这是真正的老氏之徒啊!雷君名叫雷希复,号凝和。法号为冲妙崇正法师,他是通真观的第一代祖师爷。 可见通真观始建于大德元年()。 明朝文选郎姜士望(字宗林,仪真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也有一篇通真观记(县志未选此文),被刻成石碑置于通真观内墙壁。清朝乾隆己丑(三十四年,),道士李复耘募集资金再次修缮通真观,重塑道祖之像,将原来的旧像埋葬在山门前的土岗,并且勒石志敬。 清朝陶鉴(字镜堂,邑诸生,曾参与《雍正仪征县志》编撰)记录的乾隆三十九年()春王正月所记的《通真观记》,县志有所摘录。其中说到: 真州旧江口的通真观,起源自汉、唐,历史悠久,本地有位卜翁,是开创通真观基业的人。经历了多少年的兴衰,到了元朝的至元年间,五老峰人雷希复道长,访师问道来到了仪真。当时孚惠先生寓居在新城,离通真观大约一里多路,雷希复经过问卜和考察后,开始大兴土木,修葺了观门、修缮了玉皇殿,增建了道祖堂左右的丹房,连厨房、浴室、宿舍等都包括在内。另外,还建成了道房若干间,以便前来云游的道士和远道的信众住宿休息。环整个通真观,面积很大,空地不少,溪水横流,石桥直跨,种植了元都之桃,豢养了青城之鹤。从通真观大门向外望去,浩浩长江东逝,绵绵南山逶迤。十多年后,一个崭新的通真观终于落成了,改名为“通真万寿宫”。落成后的通真观热闹非凡,高士道长羽流云集,石坛鱼磬,殿阁虚声,俨然是一座太清名观,与九宫之瑞庆宫、浔阳之寿圣观相齐名,形成当时道界三足鼎立之势。后来雷希复去到扬州发展,通真观的热闹静儿逐渐的衰落下来。 明朝洪武年间,兵部尚书单安仁退休后在珠金里养老,同意道会路通玄道长重修请求,再次开展了集资修造通真观的工程,而将仪真城里的玄妙观也并入了其中。 后来到了建文年间,靖难兵起,燕军从这里渡江,通真观被毁,只留下老君殿和前殿的大柱子,其余的建筑尽归劫火。直到弘治初年,还是这个样子。后来江潮大泛,老君殿也倒了,前殿的柱子也没了,从前的碑记石刻等物,统统都淹没在滔滔江水之中,只有可怜的老君金像,漂到了附近的村庄树下。当时有一位济宁尚书王公,让手下人前往江南购买了数以万计的木料,运送到老君像附近时,怎么拖拽牵挽都移动不了,手下人赶紧向王公报告,巧的是王公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一位老翁对他说:“你如果能把我的殿宇建起来,我将保佑你一生平安,仕途顺利。”这位王公就将自己所购买的木料,全部拿出来重建通真观,通真观又重新繁盛起来(关于靖难燕军过旧港通真观,详见《帝王过仪征之明成祖朱棣》)。 到了万历末年,江水再次泛滥,观宇建筑又都淹没了。我的叔高祖、文学嘉瑞公与他的同学高椿年,重新勘察地势,看中了都司王维京(仪真人,崇祯三年封荫都司经历)家的旧业,就花钱买下作为新的通真观观址,会同汪钺(崇祯十二年封荫武英殿中书)重建,他们采购建材、遴选工匠,建造大殿、塑造金像,按照从前的规制再造。在观前又购置了数十亩田地,用以解决通真观的日常运作开销。这就是今天尚存的通真观,也就是明朝姜士望中书所记的、天启年间重建的通真观。 明代仪真文人黄瓒有《游通真观》诗。 闭门春色有无中,作意招寻仗寓公。 花近寒江怜蓓蕾,人于丹观觅崆峒。 郊原久渴锄犁雨,樵牧新瞻旌斾风。 我亦旧人廻白首,十年修竹蔓西东。 (关于黄瓒,详见铜山《黄瓒墓》)。 县志载,明兵部尚书单安仁墓,在旧江口,通真观东隅。 单安仁墓今已不存,但单安仁对运河入江口的再造、对仪真的历史贡献,是值得为他树碑立传的。 单安仁是明朝初年的兵部尚书,《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列传二十六)有他的传,译成白话文: 单安仁(-),字德夫,濠人(濠州,即凤阳)。年轻的时候在元朝的地方政府里做小吏,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单安仁组织义兵,保卫乡里,后被元朝政府授予“枢密判官”,跟随镇南王孛罗普化守扬州。针对当时群雄四起的形势,他说,别看到处都是队伍,他们不过都是被人驱使利用罢了,成大事的王者与他们肯定不一样。 (镇南王孛罗普化收编了张明鉴的长枪军,张明鉴要推举孛罗普化做皇帝,孛罗普化不肯)长枪军赶走了孛罗普化,单安仁不愿跟张明鉴混,听说太祖(朱元璋)当时已经占据集庆,认为这是自己合适的领导,就率众归附,太祖很高兴,命他带兵去守镇江。他管理队伍严明,敌人不敢侵犯。后派他去守常州,期间他的儿子投降了张士诚。太祖了解单安仁忠谨性格,对他非常信任,用人不疑。还升他做浙江副使。(在龙凤六年闰五月已废除“寨粮”这一义军初期筹饷手段的情况下)军中有将帅仍以“寨粮”的名义搜刮欺压百姓,单安仁严格执法,后升为按察使、中书左司郎中,协助李善长裁断。调任瑞州守御千户,再后来调入中央,为将作卿。 洪武元年(),提升为工部尚书,既领兵又做工程。单安仁很聪明精于计算,领导建造的诸多工程,无论大小,都很符合太祖的心意。一年后改任兵部尚书,因年老请求还乡。太祖赐给三千亩田,七十头牛,每年发给尚书俸禄的一半。洪武六年()授职山东参政,单安仁恳切推辞,得到许可。退休期间,曾上奏请求疏通仪真南坝至朴树湾的水道,以便利官民运输,疏通运河江都深港以防止淤塞,迁移瓜洲粮仓至扬子桥西,以免受大江风潮的侵害。太祖认为他的建议很好,再次授予他兵部尚书,他坚决致仕退休。 明初的时候,尚书官阶是正三品。洪武十三年()中书省撤消后,尚书升为正二品,但单安仁致仕在此之前,太祖念及安仁的功勋,洪武二十年()特授予他为资善大夫。是年十二月,单安仁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明太祖实录》也有记载,原文: 兵部尚书致仕单安仁卒。安仁凤阳人,岁壬辰招集义兵保乡里,元授枢密院判官,丁酉从镇南王孛罗普花守扬州,镇南王为长枪军所逐,安仁遂率所部渡江来附,授元帅,命守御镇江,戊戌授按察司副使,辛丑升按察使,甲辰擢中书省左司郎中,乙巳调瑞州守御千户,吴元年入为将作司卿,洪武元年拜工部尚书,二年调兵部,辞归,六年召为山东行省参政,辞不受,八年再授兵部尚书,致仕。家于仪真,是年十月特授资善大夫,至是卒。上遣礼部主事盖霖致祭,仍赐赙钞一百锭。 《明太祖实录》上的简历与《明史·列传》内容基本相同,但后面几句较详细:单安仁致仕后“家于仪真”;去世后太祖派礼部主事盖霖致祭;还拨付了丧葬费锭。 县志上也有单安仁的传,与明史有补充之利。译成白话文:单安仁,一名居仁,凤阳人,胡《志》、陆《志》作“定远人”。元末招集义勇保卫家乡,号称“青军”,自称元帅。后来军粮匮乏,移军维扬。太祖占据金陵后,单安仁率众来附,太祖赞许他的诚意,授他官爵,让他带本部兵马守常州。单安仁忠诚于太祖,多次征战立下战功。他的一个儿子在常州叛降张士诚,后来太祖军攻克苏州,活捉了这个儿子,太祖将他交给单安仁,由他自己处理,这是太祖以老乡的情谊照顾单安仁啊。单安仁累官兵部尚书,致仕后在仪真居住而占籍。仪真的很多工程设施、衙门建置,都是在单安仁的倡议下设置的,惠泽整个仪真,至今还享受着他的好处。单安仁洪武十九年卒(明史为二十年),太祖赐祭葬。 退休后的单安仁居住在仪真养老,他于洪武二年()从兵部尚书职位上致仕,时年67岁,洪武二十年()去世,享年85岁,在仪真生活了18年。 县志记载,他的家“单尚书第”位于单家桥北,而单家桥,正是因他而得名的。县志还载有明高搴单家桥《晚步》诗: 绛云舒卷暮虹遥,柳色笼烟尚未凋。 正是画楼寥寂后,惊鸦喧起夜来潮。 经笔者多方探访和结合史料考证,单家桥位于今市区天宁巷,天宁寺与实小幼儿园交界处。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人。官至知制诰,主修《元史》)撰写的《凤阳单氏先茔碑铭》中说,“公退卜仪真珠金沙,结庐以居。”县志在记载旧港通真观时,也有“尚书单安仁退老珠金里”之句,珠金沙、珠金里都是宋代对旧港一带的别称。综合起来看,单安仁在仪真至少有两个家:城里的在单家桥,城外的在旧港。 单安仁是仪真明清大运河入江口的再造者,他为明清漕运和两淮盐运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仪真从明初到清后期近五百年的繁华,亦赖于此。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列传二十六)记载,“家居,尝奏请浚仪真南坝至朴树湾,以便官民输挽;疏转运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浅;移瓜洲仓廒置扬子桥西,免大江风潮之患,帝善其言。” 《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比较详细:洪武十三年(),致仕兵部尚书单安仁言:“大江入黄泥滩口,过仪真县南坝,入运河。自南坝至朴树湾,约三十里,宜浚,以通往来舟楫。其湖广、江西等处运粮船,可由大江黄泥滩口入运河;其两淮盐运船,可由扬子桥过县南坝,入黄泥滩出江;其浙江等处运粮船,可从下江入深港,过扬子桥至运河;凡运砖木之船,皆自瓜洲过堰,不相混杂。如是,则官船无风水之虞,民船无停滞之患。” 宋代漕运曾经达到史上峰值,年漕万石,在真扬运河上诞生了世界最早的船闸——乔惟岳二斗门和陶鉴真州复闸。进入南宋以后,宋金、宋元战争不断,漕运量减少,运河入江口逐渐浅涩,元代大部分时间依仗海运,加之在真州入江口涨出了黄泥滩,所以部分槽盐运输转往旧江口(旧港)或瓜洲。 明初单安仁定居仪真后,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向朝廷提出了整治运河的综合性方案:打通运河入江口,挑浚大江经黄泥滩连通宋运河的玉带河,修复宋运河三闸(清江闸、潮闸、腰闸);疏浚堰河(里河),建天池、五坝;全面疏浚从运口经朴树湾到扬子桥(今三汊河)的运河河道。 单安仁在仪真建设的水利设施: 1、疏浚城南坝经朴树湾至三汊河的运河。这项工程很大,运河线路有四十里。 2、重修宋三闸。南宋嘉泰二年(),真州知州张頠在北宋陶鉴真州复闸(木闸)的基础上修建了石闸(潮闸、腰闸),嘉定年间真州官员又建了清江闸,明初这三闸已不能用。洪武十六年(),单安仁主持重建。“以蓄泄水利,以分行漕舟。盖宋故道也。” 3、新建五坝。在县东南三里曰一坝,相接曰二坝,又南曰三坝;又东一里,相接曰四坝、五坝。明洪武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筑。土坝皆以数名,各疏支渠,以达通江大河。凡荆湖、江浙诸路官民舟及漕饷进京者,悉抵坝下。遇水涸闭闸,则舟于坝上辘轳过之,佥夫役四百五十人。又三岁一挑,港夫凡九千二百馀人。后,四闸之利兴,遂弃不复用。明吴与弼《泊仪真坝下》诗: 坝上停篙转柁楼,江边解缆别真州。 满怀秋思无心写,独看岷峨万古流。 4、整治玉带河、堰河,形成天池。因疏浚黄泥滩和建设五坝,整治了宋运河与黄泥滩的连接线——玉带河,整治了五坝与运河的新的连接线——堰河(里河),形成了天池,使得运河与江口之间有了闸、坝两条通道,水多过闸、水涸过坝。 5、銮江桥,在城东十里,新城。洪武中,单安仁建。 6、太平桥,在北东十里。洪武初,尚书单安仁造。 经单安仁请示,朝廷在仪真设置的衙门: 1、批验盐引所。淮盐在仪征制掣,唐宋就有,但批验盐引所这个机关,始建于元大德年间,位于真州;洪武初年,建于瓜洲;十六年()夏,单安仁建议,诏大使侯奎移建于县南二里,在一坝、二坝间,隶两淮转运司。清康熙二年(),巡盐御史张问政将察院也搬到盐所。 2、水驿。旧为迎銮驿,在县南一里,即建安故驿,仪征卫址也。明洪武元年()春,驿丞张中肇建。后,病其非通衢,十三年()秋,驿丞张让始请移城外。按,旧驿,洪武初尝建于瓜洲。是时,因兵部尚书、邑人单安仁建议,乃迁隶于县。本驿原额站船十七只,船头三十人,马头十六人,水夫一百七十人;驿站马十二匹,上马二,中马六,下马四。上、中、下铺陈八十副。 3、递运所。在水驿东,洪武三年()初建于瓜洲,盖扬子旧属。洪武十六年(),单安仁建议,诏大使姜以敬移建于此。本所原额座船十二只,红船四十七只,铺陈五十九副。额设水夫六十六户,外水夫四百十三名,防夫三十名,与驿夫并本府所属州县,每年徭编应役。 4、批验茶引所。在县南二里,清江闸西。宋初,置茶务于真州榷税。明洪武初,创于瓜洲。十六年(),单安仁建议,请开河道。诏大使析鼎,移建于此,隶扬州府。 5、巡检司。原在县东南十里旧港。洪武元年()巡检水璧肇建;十六年()兵部尚书单安仁建议,令巡检白敬移置县南三里晏公庙东北汊河口。司设吏一人,弓兵六十人。每岁,俱府属州县徭编,解发应役。 单安仁在仪真修建的庙宇 1、晏公庙。在巡检司西,在陈家湾。洪武间,尚书单安仁建,盖司水之神(详见真州《晏公庙》)。 2、通真观。即通真万寿宫,在县东南十五里,新城旧卧虎闸南半里。元大德间,五老峰人雷希复建,后颓。洪武间,单安仁令通会路通玄重建(详见本文上半部分)。 单安仁还有位死忠叫“毕了”,跟着他起义加入青军,最后随他来仪真,任世袭“右所百户”。县志卷二十五职官志的《明卫指挥使以下世袭表》之“右所百户”分表,记载毕了是临淮人,跟随单安仁的青军入明,被授百户一职。县志记载了他世袭七世,其中第四世毕升在天顺年间曾参加征交趾,升副千户;第六世毕献在正德年间以巡江官身份追捕盐枭不幸殉职,被列入县志“忠烈传”。 单安仁为仪真做了很多好事,然而他的生后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县志载:“单尚书第,陆《志》云:“在城中单家桥北,兵部尚书单安仁居也。嘉靖《志》云:‘子姓零替,今无存者。闻之老人言,数十年前,犹有一门欹焉。今灭其迹。’”就是说单家在仪真嘉靖后已经找不到后人了。对于“生后落寂”这个奇怪的现象,清代仪征文人厉惕斋在两首诗中有猜测。 厉惕斋《真州竹枝词》景阳楼诗: 共乐盐门今夕开,有人楼下独徘徊。 可怜如此繁华境,阁老全家换得来。 诗后有注:传说向掣盐在瓜洲,胜国单阁老安仁悯邑人辛苦,移此,朝廷以擅专,故全家受戮。或曰瓜洲盐枭乘乱,戕及全家。二说未知孰是,志乘不载,无可考矣,今单家坟犹存。天宁寺东北尚有单家桥,父老云:附近即单公府邸也。 厉惕斋《真州竹枝词》天池诗: 阁老祠前散晚烟,可怜香火已萧然。 茫茫一片天池月,昔日屯船今钓船。 诗中有注:传说仁寿桥南,土神纱帽红袍,乃邑人哀阁老死,私祀之,而讳曰福祠。 厉惕斋自己声明,对单阁老生后落寂的猜测是“传说”,而且传说是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淮盐原来是在瓜洲制掣,单阁老觉得仪真人“辛苦”,移到仪真,朝廷认为他擅专,杀了他全家;另一个版本是,淮盐制掣移到仪真天池,损害了瓜洲靠盐吃饭者的利益,盐枭乘乱来杀了单阁老全家。不管哪种原因,仪真人对阁老的死很伤心,但却不敢公开祭祀,只是在仁寿桥南建了个福祠,供奉纱帽红袍的土地神,其实这位土地神,就是单阁老。 笔者分析,这两个版本都不靠谱。一是朝廷杀他全家史书未载,将掣盐从瓜洲迁往仪真事实证明是对漕运、盐运有利的,是功不是过,不可能因此获罪;二是瓜洲盐枭来仪真杀人,可能性极小,即便得手,也不妨碍邑人为他建祠立祀,没有必要偷偷摸摸“私祀之”,更何况还有太祖赐祭葬。 从宋濂《凤阳单氏先茔碑铭》中可知,此文是宋濂在单安仁72岁时撰写的,单安仁字德夫,自号宁山,娶赵、芮二夫人,生子凡七:单鉴、单铠早逝,单锧擢皇陵卫千户所镇抚,单钺、单钓、单铭、单铨,“皆亦崭然见头角矣”。时间是洪武八年()。 笔者在网上与阜宁网友单国荣等讨教切磋,他提供了一则重要的信息:单安仁的女婿是全宁侯孙恪(kè),死于蓝玉案,单安仁生后落寂很可能与蓝玉案有关。 查《蚌埠市志》,单安仁老家为今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孙嘴子村,“兵部尚书单安仁与燕山侯孙兴祖连亲”,确有其事。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列传卷二十一有孙兴祖和孙恪的传,孙兴祖也是濠人,跟随太祖渡江攻取和州,屡立战功升天策卫指挥使。后随大将军徐达攻泰州、取通州、镇彭城、克大都。洪武三年()跟随徐达出塞,战死,年三十五。太祖悼惜,追封他为燕山侯,谥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 不久,中书省入奏都督同知汪兴祖的事,太祖听到汪兴祖,联想起孙兴祖,叹息之余,命给故燕山侯兴祖家月俸,让他的长子孙恪袭武德卫指挥使,后来又做都督佥事。洪武二十一年(),任孙恪为右参将跟随蓝玉北征,获捕鱼儿海大捷,论功封全宁侯,岁禄二千石,予世券。 孙恪谨敏有儒将风范,洪武二十五年()进兼太子太保。后来去山西跟随宋国公冯胜练兵,不久召还,赐他宅第在中都凤阳居住,后来蓝玉案发,孙恪被打成蓝玉一党,处死。 单安仁洪武二十年()去世,蓝玉洪武二十六年()案发,单安仁女婿孙恪因蓝玉案被杀,离他去世仅相差六年,所以单安仁除了赐祭葬,死后没有其他荣誉,用这个理由能解释得通。 网上还有固始单氏家族的资料,说有一支“单家栗林支”:始祖单定家(单安仁次子,又名单百官,由凤阳迁居往流集西白露河旁,葬往流单小庙)、单定永(单安仁第七子)、单定久(单安仁第八子),他们兄弟三人于洪武元年()年9月迁居固始县偏远的往流集西白露河附近居住,因不远处有一片野生栗林,后人叫单家栗林。他们的子孙除部份留在固始外,大多外迁淮河以北、安徽等地。 为何单氏三兄弟会流落固始?原因是单安仁有一子投降了张士诚,疑怕遭朱洪武诛灭,便举家外迁,将其八个儿子分散隐居(宋濂《凤阳单氏先茔碑铭》记为七个儿子)。另因当时定永、定久年幼,定永由舅父周氏照顾指导生活,后改姓周;定久由姑父许氏照顾指导生活,后改姓许。当地就有了单、周、许一家的说法。当兄弟三人成人后,合力在往流朱皋大寺西建祠堂“三官庙”为家庙,取堂号“忠义堂”。庙内供奉单氏祖宗牌位和圣像,老祖爷单安仁的画像在清末期间被山东单县请去。现在三官庙随岁月磨蚀,地名犹在,圣物不存。 固始单氏家族的说法,不论真假、有没有依据,都无助于解释单安仁生后落寂的问题,他有个儿子投降张士诚,太祖是知道的,抓到了以后交给单安仁自己处理,足见信任。单安仁去世后赐祭葬,也是证明。 单安仁墓有三种说法,笔者觉得,还是以《明太祖实录》为准,就在仪真。 笔者认为,导致单家后人隐名埋姓、官方也不能对单安仁建祠立祀的原因,是单安仁死后六年,其女婿孙恪卷入蓝玉案。蓝玉案是谋反大案,不仅在明朝未获平反,在清朝也没有。但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在仪真仁寿桥南建了福祠,明为供奉纱帽红袍的土地神,实为祭祀单阁老。 笔者建议,在南门天池、大码头一带,建单安仁纪念馆或雕塑,让大家都记得和感恩这位为运河入江口和仪征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贤。 巫晨
|
当前位置: 剑阁县 >探访仪征古迹之旧港通真观
时间:2021/8/26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九家顶级度假村,掀起近距度假风潮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